过去两年来,我懒于写作,疏于同先前共事过的编辑联络,于是我向今年威尼斯双年展郑重提交的媒体申请旋即被忽略。我对艺术的胃口还没好到要花250欧元买张金卡、让我可以在开幕三天内畅行无阻,那也就更别提价格翻倍、好处零碎的白金卡了。因而,即便我对这出欢愉的马戏恋爱有加、无法免疫,我的威尼斯之行仍然差一点儿就未能成行。就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一名策展人邀请我参加一个平行项目,于是我欣然接受了邀请。还有,到达威尼斯的前几天,《燃点》编辑部邀请我为他们撰稿(很有可能是因为本来说好的作者生病或爽约了),稿费足以支付我在当地的住宿费用。今年我不太走运,没能蹭到一张沙发,只好租了一间迷你公寓,结果房间里能挤下多少人就来了多少人。
我到威尼斯的第一个早晨,先去朱代卡岛(Giudecca)散了个步,我的一个好朋友请我去一家叫“猎手”(I Cacciatori)的餐厅吃午饭。我们坐在运河边,挨着一座桥,河对面就是圣马可钟楼。我竟然吃着铺在鹰嘴豆泥上的娇嫩碳烤墨鱼,我朋友点了兔肉配蘑菇。我喝白葡萄酒,他喝红葡萄酒。我们还细嚼慢咽地吃光了一道奶酪拼盘,喝着不同的葡萄酒,餐后又喝了一杯咖啡,酒足饭饱地又坐着聊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聊的尽是威尼斯的生活,说这儿的生活如何如何与三百年前没什么两样,在那些紧闭的门后如何如何藏着硕大的宫殿,都挺神的。我们试图一一历数当地泻湖里生长的各种贝壳。我们相互讲述着无数个无尽无声的夜,这座美妙城市的多情历险。
写到这儿,我试着让自己觉得威尼斯之行不去不行。有关此届双年展的主题“全世界的未来”你肯定能从很多其他文章读到有关它的介绍,我也会写到。我还发誓会认真研读策展人Okwui Enwezor名字的发音以将功补过。
在花园(Giardini)展区,加拿大馆显得利落且暗藏机关。其中展出的装置来自三人艺术家组合BLG,由脚手架支撑,就挨着英国馆,乍看上去像一座花园洋房里的树屋。它的第一间展厅放着一家魁北克省街头小店的复制,标价牌的字样越接近出口越模糊,而出口就在山坡的后面;很多人肯定还宿醉着、头昏脑胀、且极度渴望立体脆和香草可乐——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唯一的抱怨大概就是:没法在这家商店买东西。

BLG’s installation for the Canadassimo Pavilion
威尼斯人对游客的粗暴是出了名的,即便游客就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收入来源。目中无人的威尼斯人主要有这两类:拒绝帮你把三明治一切二的侍应生,和为了抢水上巴士的座位而几乎要把你挤出去的领养老金的人。千万别掉到运河里去;在这混沌的柔波下,躺着五百年来不小心从桥上或船上跌落河中的醉汉们,以及两艘苏联潜水艇、一艘宇宙飞船、前几届双年展在每届11月时过期作废的所有艺术品等深水怪物们。

莎拉•卢卡斯把整个英国馆的内墙涂成了亮黄色,其间点缀着几座人形雕塑,挺着各自的生殖器,或在屁眼里插根烟。用我室友的话说,这件作品与这个艺术家就是在尖叫着:“这就是性!粗鲁得很!丑恶的性!看着它!敢不敢你,看着它!”好了,莎拉,我们看着它,就像看一桩事实那样看着它,我们还挺享受地看着它,其实真的没有尖叫的必要。不过还是要感谢你莎拉,在介绍文字里提到此次英国馆创作的灵感来自于“漂浮的岛屿”;这是我最爱的甜点之一。我还想向你道歉莎拉,因为我冒昧地直呼你的名字,就好像我们是朋友一样,讲话还这么拿腔拿调——态度实在太恶劣了。

Sarah Lucas’s smoking asses at the British Pavilion
我看了不少演出,其中一场是一个女人坐在一把假电椅上,另一场是一个在绳网上假装成蜘蛛攀爬的人,还有一场是一个戴着兔子面具的全裸的人。除了望着裸体盯得出神外,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们连着赶场子,看到后来,觉得和平时地铁外面的街头艺人没什么两样——可惜他们连演奏手风琴或转溜溜球的手艺都没有。
不过,我很欣赏这一幕:一支特种部队从一艘快艇上一跃跳到了花园展区的正门口。六臂男飞速排成一列,站到拥挤的人墙前,哈哈大笑着组成了一座人形金字塔;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坐回到快艇里,来得快去得也快,消失在运河的远处。这是由Harold de Bree和Mike Watson编舞的《爱神机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后来有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这支特种部队被真的意大利警方扣留审问。

在漫长疲惫的一天后,和我坐着一起喝酒的还有几名艺术冲浪者,其中一名来自法国南部的画廊主对我说,她觉得整场双年展太自恋了、自恋得令人压抑。她说艺术必须为人而作,这些人不拘于创作的过程,也不应从其本应反思的空间与世界中抽离出来。我不能同意更多;不过我也在想,如今连一名画廊主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么真的到了当代艺术进化的临界点,要么她就是在怨愤她所代理的艺术家没有一个被选入这次的双年展。
在你已经读过或听说的有关德国馆底楼艺术家Hito Steyerl的创作描述之外,我没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我建议你最起码去看两次,坐在椅子上享受这房间的塑胶味。真的很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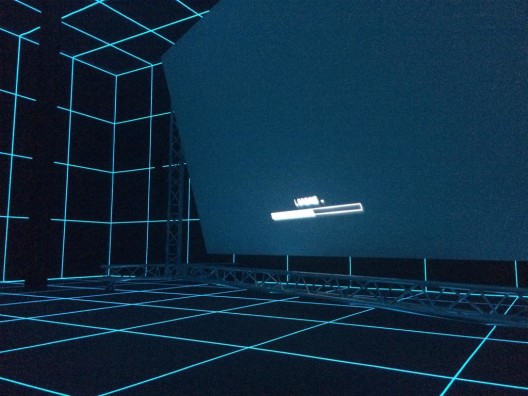
在你开始觉得精疲力竭、却又不能离开花园或军械库展区(Arsenale)而显得自己没教养时,我向你推荐以下歇脚去处。
首选就是法国馆,你可以靠着椅背,一边听氛围音乐,一边欣赏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的树,这棵树沿着房间缓慢地移动。迷幻森林加迷幻音乐?法国馆做得好,给了我们这么棒的调剂空间!
军械库的中转点是图瓦卢馆,你可以坐在破墙下的板凳上,享受充足的阳光,看着房间中央的一座水池缓缓冒着水汽。要是你不知道图瓦卢,我原谅你;它不过是太平洋上的一小片群岛,人口仅12,000,然而它变得渐趋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这座星球的作恶多端都在它身上显现出来:几年之后,这片岛就会因为全球变暖而被完全淹没。讽刺的是,图瓦卢的碳排放是零,即便是这座由台湾艺术家黄瑞芳设计的赏心悦目的展馆,也会在双年展结束时被完全回收,而其相关资料将以数字形式呈现,并使图瓦卢成为威尼斯首座纸上智能馆。

Vincent Huang’s installation for the Tuvalu Pavilion
Bauer酒店里Loulou的临时空间举办了由两名艺术家组织的鸡尾酒派对,作为他们的婚礼,参与庆祝的到场人士并不多(我甚至不知道也不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现场还有伦敦时髦艺术会所Gazelli Art House带来的几件精美装饰作品,人们穿得跟长颈鹿一样,喝着喝不完的Americano鸡尾酒。一点点创意加上很多钱,这就是我在威尼斯去过的最棒的一场派对。
意大利馆:不。
中国馆:不。
一幅满是全球各种蜜蜂的画作把我吓得半死,因为我对蜜蜂过敏;所以我再也没法集中精神看比利时馆的其他展品了。

话说回来,当天晚上的派对却让我十分受用;披萨,啤酒和电子乐。
出于对水上巴士票价不公平政策的忿恨(当地人买单程船票只要1.3欧元,游客却要付7欧元),我到威尼斯的第一天就赌气一张船票也没买。但我显然已经不那么年少轻狂了,我也很怕检票员真的逮住我,把我拖去地牢,连对泻湖之美、阳光之暖也毫不在意。于是我终究向这票价政策投了降,很不情愿地花30欧元买了一张双日票。不过一旦钱花出了手,我倒反而举着票屁颠起来,不管去哪儿都要做船。然而在我坐最后一趟水上巴士时,兴奋也消退殆尽,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朝着检票员炫耀我的票了。
日本馆的天顶垂着很多钥匙和红线,让我想到纽约东村的一家印度餐厅,那家餐厅的天花板装饰着很多红辣椒之类的小玩意儿。如果你去的那天正好(或假装)是你生日,侍应生就会关灯,放舞曲,送你一碗插着一根蜡烛的冰激凌。

政治的威尼斯:
威尼斯古根海姆美术馆聚集了一大群抗议者,他们谴责美术馆拖欠波斯湾酋长国阿布•扎比新馆建造工人的工钱。
乌克兰的抗议者穿着写有“正在度假”字样的军装涌入俄罗斯馆。
冰岛馆,瑞士籍艺术家Christoph Büchel把千年教堂Santa Maria della Misericordia改装成威尼斯的首座清真寺,在本地人中激起了骚乱,却从穆斯林群体收获了不少赞扬,让他们在步行距离内有了周五祷告的美丽去处。
一个因情绪多变而出名的艺术公关透过自己手中的一杯起泡酒笑了起来,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前牙,动情地转着眼珠,转得过久了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试图在这儿看到一些艺术。”
我在瑞士馆Pamela Rosenkranz自己的作品前见到了她本人,我们握了手,我对她表示祝贺。她看上去有点尴尬、有些害羞,在我问她有关创作的问题的时候,她不看我的脸,而是看着我的肩膀。她的作品是一座装满了粉色带气液体的游泳池。她穿了一件深蓝色大衣,在人头攒动的开幕式上沿着墙安静地走动。她看上去就和她的作品一样如梦似幻却潜涵着危险。
在从搭着露天帐篷的休闲吧中间的大游泳池游荡到两处鸡尾酒吧,再踟蹰到一处大舞台(一名穿着紧身短裙的大胸女子唱着上世纪90年代的劲爆舞曲),我和一个好朋友最后还是决定坐在瑞吉酒店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一名热心的侍应生在这片露天客厅找到了我们,并很周到地带来四瓶不同的好酒让我们选用。我们已经从自助餐室拿了不少好吃的摆在面前,我们边聊边吃美味的帕明森芝士烩饭,番茄色拉,油炸橄榄塞肉和一盘冷切肉。此时是下午2点,我们打算再过半小时就出发探索剩下的荒凉之地。

这一定是整场双年展最豪华的开幕派对;土耳其充满了惊喜。在这享受放松的片刻,我们的思绪回到了Sarkis,这名今年代表土耳其参展的77岁亚美尼亚籍艺术家的概念创作是坚定且严谨的,他花了一年半的时候创作装置《呼吸》(Respiro),在令人心怡的彩虹灯光、镜面与舒缓音乐之外,交叠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参照,不仅是对图像的反思,也是对材料与空间把控的精准选择。如此强有力的一件作品,如此谦逊微妙的政治力量,让土耳其当局官员决定不来参观土耳其馆——不过话说回来,今年对他们来说确实不好过,因为艺术家是亚美尼亚籍和金狮奖都给了亚美尼亚馆。
瑞吉酒店的派对则一点儿也称不上谦逊或微妙;及时行乐的气息无处不在,一点能触动政客的动静都没有。土耳其在威尼斯被奇怪地割裂成两个部分,让我们深感不安。尽管如此,我朋友和我在陷进大沙发的同时都觉得再过两小时就能回去了是种解脱,那时我们享够了土耳其人的奢华,一艘土耳其出钱租下的出租船也将把我们带离这座小岛

一如既往,参观双年展就像一场梦——永远无法适应这座城的美,她新旧的冲突。艺术和装置看得再多亦不过匆匆一瞥。我不相信任何声称严肃地看了并全部消化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开幕的三四天里就看了超过五分之一展览与活动的人。在回伦敦的航班上,出于对降落时糟糕天气的恐惧,我浅浅地睡了过去,但感觉却像是从我潜意识的癫狂中醒过来一样。空乘递给我一个装着冰冷鸡肉凯撒色拉卷的小纸盒。



